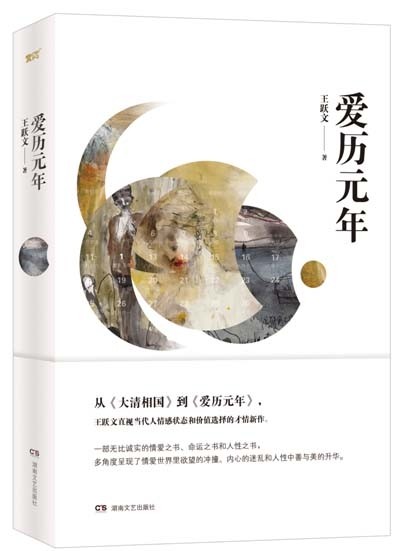第三屆常德原創文藝獎獲獎作品:
從生疏回到原點
——王躍文長篇小說包養《愛歷元年》評析
文/張文剛
一
毫無疑問,王躍文的長篇小說《愛歷元年》①是一本描述情愛的小說。書名“愛歷元年”有著耐人尋味的寄意。在人生婚戀的悲笑劇中,每小我都有本身的愛情原點,亦即“愛歷元年”,並且普通而論,這個原點或許“元年”都是美妙的、值得留念的。從這里動身,有的人不竭成長、豐盈包養網本身的戀愛生涯和心靈世界,與所愛的人聯袂到老;有的人漸行漸遠,終極偏離戀愛和婚姻的軌道一往不回頭;有的人在為難的人生際遇和心靈困惑中苦悶彷徨,分開原點最后又回到原點。《愛歷元年》描述的恰是后一種情況,主人公孫離和喜子,這一對曾有過甜美戀愛的夫妻,在工作上苦苦奮斗,一個成為了專門研究作家,一個成為了年夜學傳授,可謂風景之至,可是在戀愛婚姻的旅途上卻經過的事況了從浪漫詩意的極點跌落感情冰點,再到自我救贖、回回原點的波折經過歷程。就像他們的名字所暗含的那樣:由近乎團圓的無法到回應版主原點的欣喜。這看似簡略的回回,實則是一種超出,是經過的事況恩仇風雨和心靈磨礪之后的自我凈化和自我完美。
進進婚姻圍城后,孫離和喜子似乎剎時就變得“生疏”,成為了生疏的熟習人和熟習的生疏人。“他倆甜美了沒多久,漸漸就開端打罵。年夜事也吵,包養網大事也吵”,乃至“有時辰會忘卻爭的是什么,歸正擰著對方就是贏家”。這種夫妻關系日趨嚴重和生疏的成果,就是各自有了婚外愛情。于是兩性之間的親近與生疏被敏捷置換。孫離與李樵由於“采訪”瞭解而情感閃電升溫,旋即走進兩心相悅的狂風驟雨;喜子和謝湘安由于同事關系,在經過的事況幾回偶爾事務之后,隨即卷進兩性狂歡的大水。包養網本應屬于夫妻之間的各種親昵和繾綣,由于夫妻之間的“生疏”而轉移到了“他者”身上,“生疏人”似乎不需求太多的過渡和展墊就成為了“寶物”和“親人”。夫妻之間的生疏不只加深了彼此的隔膜和婚姻關系的危機感,同時還衍生了副產物:怙恃和兒子之間不竭加劇的生疏感;對本身身材和心思的生疏感。在怙恃沒完沒了的爭斗中,兒子變得越來越冷淡和背叛,也越來越生疏。在嚴重的夫妻關系以包養及樂此不疲的婚外愛情中,孫離漸漸對本身的身材覺得“生疏”,前列腺,掉眠癥,使他“越來越不克不及把持本身”;喜子經常繁殖的一些希奇的動機和設法,使她對本身的心思認識覺得“生疏”,本身變得都不熟悉本身了。古代社會,人生仿佛就是如許一個不竭被生疏化、甚至被同化的經過歷程。生疏化以及感情的轉移,當然有著各種緣由。起首來自于人的一種包養“古代性焦炙”,古代社會所宣示的諸多分歧理、不公正的景象,以及加在人身上的各種壓力和約束,在轉變人的心情和命運的同時,也使人尋覓符合本身的道路開釋心坎的重荷,以求得臨時的心思知足和欣慰。其次是一種社會風習和潮水的影響與裹挾,隨同經濟成長和文明提高,人們越來越追逐對財富和聲色吃苦的占有,也越來越損失了保護幸福和固守品德底線的才能。再次從更內涵的方面來看,是人的固有心思和欲看的驅動,見異思遷的人道弱點和欲看的禍不單行,假如不加以控制和防范,則必定轉變人的生涯鏈條和心靈生態。
歸納人生的生包養網疏感和荒謬感,當然也能表示出作品的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愛歷元年》的寶貴之處更在于,作包養家符合邏輯地描述了人物的感情“回回”,并由此轉達出一種暖和的氣味。心靈生態的掉衡,也唯有借助心靈的氣力來調理和修復,才幹到達新的均衡與協調。當喜子陶醉于婚外愛情帶來的喜悅和奧秘的時辰,心坎的愧疚和懊悔也把她推向了人生選擇的十字包養網路口,在顛末心坎深處非常苦楚的掙扎之后她漸漸回回到安靜的家庭生涯。絕對于喜子的“自動退卻”所浮現出的決盡姿勢,孫離表現出的是一種“主動回回”的無法,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在孫第一章(一)離的婚外愛情中,合與分就像一場“醉酒”的宴會,醉不需求來由,醒也不需求來由。當李樵提出“分別”的時辰,孫離墮入了主動的為難和極端的苦楚,而在李樵那里則是安靜包養網的、無所謂的。熟習、親近的人剎時又變為生疏。這是一個值得思慮和詰問的經由過程婚戀表現出來的“古代性題目”。作家并沒有賜包養與小說中的人物更多的品德評判,只是讓人物包養網在本身生涯邏輯的歸納中往熟悉本身、反思本身,從而調劑本身;也唯有本身的檢查和調劑,才足以投射出魂靈深處的光線。這一點在喜子的身上表現得更為充足和徹底。小說最后用“錯”和“病”來終局,是一種瓜熟蒂落的客不雅描述,當然同時又是一種態度:有錯就得“糾錯”,有病就得“治病”。孫離和喜子的兒子誕生時由于病院錯誤與他人家的孩子“錯抱”,不只僅是親情關系的錯位,也指認了孫離和喜子自成婚后情感的背叛和錯位,因此帶來一系列的后遺癥;要擺正地位,不是簡略的交流或回位,還需求持久的心思勸導和改正,這有一個艱巨的經過歷程。小說借孫離的弟弟孫卻身材上的“病”以及病痛之后的年夜徹年夜悟,現實上暗示人的收縮的、掉范的欲看也是一種“病”,一種更摧殘人、熬煎人的病。孫卻的病除了就醫外,村落游歷成為了他身材康復的一劑藥方;異樣孫離和喜子心思上的“病”除了從外界斬斷病源外,還需求“心靈鄉土”的靜養和滋補,那種來自記憶鄉土的渾厚良善和心靈與人格深處的明哲保身和品德操守是防治息爭除心思疾患的“漂亮山川”。孫離和孫卻兩兄弟的名字也預示著他們到頭來離卻、了卻情場、商場甚至于宦海的各種長短和羈絆,回回原來擁有的安定幸福的生涯。王躍文在近年的一次訪談中曾說本身誕生于村落,對鄉土懷有深摯的情感,“正脈脈含情地回看著村落”②。這也許意味著作家今后的創作就題材和價值取向而言會有所轉向,《愛歷元年》應當說就是這種轉向的開始,漂亮村落,包含心坎深處的鄉土記憶和天然神性都在號召著作家“還鄉”。
二
《愛歷元年》借男女之間的情愛之旅,表示包養網了豐盛的人道內在。小說中有如許一個精妙的比方,當他人猜忌孫離的推理小說的意義時,“他感到這個世界就像放多了洗澡露的浴缸,人坐在里面看到的只是厚厚的泡沫。他的寫作就是要撇失落浴缸下面的泡沫,直抵水底本相。”引申來看,《愛歷元年》就是要撇失落情愛的以及各種人生世相的“泡沫”,直抵人的原來臉孔和人包養網道的本相。王躍文被稱作“宦海小說第一人”,他自己并不認同,由於他以為本身“寫的不是宦海景象,而是宦海人生,是社會生態體系”③。“宦海”只是一個題材的進口,人生百態組成的社會生態體系才是文學表示的舞臺;從這個意義上說,《愛歷元年》和王躍文的宦海小說是相通的,都是經由過程情面圓滑表示“社會生態體系”,只是這里的“宦海人生”,被置換成常識分子的感情過程。與權利欲看、物資欲看等一樣,感情欲看也是以占有和吃苦為目標。這種欲看,用小說中的一個物象來描述的話,就是“螞蟻”:“一只螞蟻正順著樟樹皮的裂紋,急促地往上爬”,欲看的螞蟻,老是在殘破的處所包圍和攀升。跟其以往的小說一樣,王躍文重要把筆力投向“人道的暗角”,提醒和批評人道的弱點。正如小說中主人公欣賞蘆葦風景時看到的一首打油詩所寫的那樣:“蘆葦雖美景,警惕躲暴徒”,人恰是如許的“蘆葦”,莽莽蒼蒼,蘆花飛揚,而心靈深處也許躲著“暴徒”。《愛歷元年》就表示了“暴徒”在人心坎里的冬眠、捋臂張拳以及對品德底線的跨越,無論是夫妻、戀人之間,仍是伴侶、長幼之間,作為人其真正的的一面如謠言、假裝、嫉恨、冷淡、揣測、警惕眼、小手段等各種心思認識和行動舉止被絕不粉飾地勾勒出來,成績了豐盛、平面的人生畫卷。
小說在表示“人道的暗角”的同時,也在盡力挖掘“人道的光線”,并力求借此照亮人道的幽暗。喜子的覺醒和警醒,在情欲眼前的決然止步;孫離的自願接收分別,在忍耐苦楚之后對包養網暖和實際的切近和融進;孫亦赤流落途中對親人的掛念和念想,對“回家”的詩意吟唱;孫卻解脫名利場,回回清凈生涯的暢想,等等,都是一種人道的包圍,走出心靈“暗角”的一種盡力和尋求,都是值得確定和稱道的。當然,這種包圍是極端艱巨的,是一種自我斗爭,一種心靈搏斗,要以就義小我的快活和不受拘束為價格。這種免于沉溺和撲滅的自我救贖,是自我反思和批評的成果,是穿越心靈暗區的一縷晨光,扶引人達到加倍敞亮而美妙的世界。王躍文曾談到“敬畏”,他說,敬畏既有古代人的自我束縛,也有古代人的自我救贖。這是一種品德氣力的外化。有崇奉、有準繩的人才會有所敬畏。良多人把一切的信條都廢棄了,沒有任何準繩和品德底線,只剩下欲看。欲看像一個至尊魔咒,人成了欲看的奴隸,成了權、錢、色的奴隸以一起去旅遊的機會,果然這個村子之後,就沒有這樣的小店了,難得機會。”。有敬畏的人也是一個能自我熟悉、自我檢查的人。人有欲看是現實,但人的美與性命的價值則往往是超出這種“唯實”后所表示出的不受拘束與莊重,人需求對自我停止清洗④。可以說《愛歷元年》表達的就是如許一種欲看掉范之后對性命和感情的“敬畏”,經由過程自我熟悉和自我清洗后達到一種“不受拘束與莊重”的性命境界。
假如依照以後某些風行小說的寫法,完整可以寫成一個夫妻團圓的喜劇,或許婚姻重組的笑劇或鬧劇,可是王躍文沒有依照這個俗套來構想包養,而是在概況一池靜水實則波翻浪涌的節拍和韻律中,寫了一曲夫妻彼此背叛之后又和洽如初的正劇。作者以一種安靜、帶著幾分純凈和浪漫的情懷與目光來對待和描述情愛生涯,因此就沒有那種低俗和俗氣的風格,即便是戀愛空想和性愛描述,也顯得較為蘊藉和內斂,甚至還有幾分詩意。好比寫孫離對異性的空想,老是隱現著“蘭花”的抽像。在他所接觸的異性中,劉桂秋、李樵、妙覺等女性都在“蘭花”的映托下,顯得楚楚動聽和值得念想。蘭花以其雅潔的氣質和清香的氣味照亮了他心坎的混沌和等待,因此對女性的空想和愛戀也幾近升hu包養awei一種正人品德和典雅情懷。這種蘊藉含蓄和詩意化的想象與表達,還表現在一種文明氣氛的營建和襯著上,詩詞歌賦、琴棋字畫、談佛論道,有時辰被恰如其分地交叉在文本中,成為對世俗生涯的裝潢、滲入和洗濯。這種詩性的、暖和的氣味,還反應在作者經由過程情愛的觸須延長到社會世相,表達對社會人生的追蹤關心和關愛。作者經由過程藝術抽像表達出來的對某些社會題目的憂慮和批評,對社會底層低微者的體恤和關心,都表現了作為一個作家的憂患認識和悲憫情懷。正因這般,當我們追隨主人公的行動踏上“回回”的旅程,向著美妙的“原初”切近和超出時,我們的心中在升騰起一股熱流的同時對社會和人生包養也會寄予無窮的盼望。王躍文曾如許剖明:“文學也許應當超逸誕生活的真正的,給人以幻想和盼望。”⑤這是作者所尋求的一種愿景,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時期所應尋求的文學幻想。
不只這般,意義還表現在藝術的層面。從生疏回到原點,也可以懂得為謝絕情勢主義的生疏化表示,謝絕那些人工砥礪和決心設定,回到最樸素、最本真和最天然的表達,應當說這也是藝術的“原點”。文學藝術的來源和生涯親密相干,自己就是生涯的一部門。近古代以來,一些作品以反感性、反次序為旗幟,經由過程變形、拼裝、夸張、騰躍等“古代”“后古代”的藝術表示伎倆,來提醒實際生涯和人道,固然也給人以新奇的審美感觸感染,但似乎和通俗人的生涯隔得較遠。王躍文的高超之處,在于以平庸、天然的筆法將簡直原生態的生涯盡情宣露,讓觀賞者沒有任何阻隔地融進其間,在感同身受中懂得生涯、感悟生涯,進而發明生涯。在他這里,也有“古代性”“后古代性”的工具,但重要不是作為一種伎倆和技能,而是一種鋒利的目光和內在的沉淀,是對生涯實質的掌握。王躍文的這種回回藝術原點的作風,不只是一種藝術涵養,更是一種創作不雅念和價值尋包養網求。
三
恰是借助日常生涯的描述,表示人的情感糾葛和心靈過程,因此在藝術構想和表達方面表現出光鮮的特性尋求和特點。往年夜一點的方面講,王躍文筆下的生涯氣味和情致有點“紅樓遺韻”;往近一點說,王躍文的藝術表示和作風可以看到魯迅的風趣、機靈、悲情和譏諷,老舍的真切而細膩的描述,錢鐘書的精妙的比方,當然還有融會實際主義精力和幻想、浪漫情懷的藝術尋求,從中可以感觸感染到巴金、沈從文、汪曾祺等巨匠的流風余韻。
從生疏回到原點,是性命和感情的跌蕩放誕與回回,底本可以在故工作節的設定上年夜做文章,可是作者偏偏沒有決心運營故工作節。夸張一點講,這是一本沒有故事只要真正的、沒無情節只要感情的小說。或許說,它沒有完全、清楚的內在的情節鏈條,只要生涯的“場域”和睦息,只要內涵的情感流和感情流。感情的產生、成長、飛騰以及突轉或突變,及至沉潛、回回而趨于安靜與和美,這就是小說內涵的情節。那些獵奇求異的讀者能夠會掉往瀏覽的愛好與耐煩,只要那種善于體驗、感觸感染、品味生涯和人生況味的人方能遭到浸染和激動,并領略小說內涵的神韻和魅力。假如借用小說中一個常用而具有動感的句式“越來越”造句的話,就主人公孫離和喜子包養網的生涯與關系而言,在小說的前部門是“越來包養越”走向嚴重和生疏,在小說的后部門是“越來越”告竣體諒與協調。這就組成小說的一種情感節拍和感情線索,從這方面來說,小說的構造是完全的,也是完善的。如許一條隱形的“感情線索”串連起來的是日常生涯的場景和瑣事,有時在這條線索的諸多節,不是來享受的,她也不想。我覺得嫁進裴家會比嫁進席家更難。點上是一種類似、雷同的生涯場景和情形的“復現”和照顧。品茗吃飯、賦詩作畫、漫步休閑等生涯內在的事包養務以及負氣爭持、懷念玄想等保存狀況和心思狀況被作者誨人不倦的描述,成為涵容感情而又過濾、沉淀感情,復原人道的“容器”。推進內涵感情成長的動力是人的欲看和對欲看的控制,這是一種“內生力”,是一種比內在的邏輯推理招致故工作節的成長而更為強盛和耐久的氣力。可以說,《愛歷元年》采用的是復原人的心思認識和欲看的敘事戰略。
正若有的學者剖析的那樣,“王躍文的小說,有著豐盈的日常生涯細節描摹與纖毫畢現的心思描繪,纖細到人物的一個眼神,一個稱呼,一顰一笑,連語調與姿態等不經意之處,他都不含混交接,而是出力刻畫。”⑥《愛歷元年》作為一部感情小說、生涯小說,當然就更重視心思描繪和細節描述。文本中有大包養批的心思感到和心思實際的描述,這種描述把心思和“此在”與“彼在”聯絡接觸在一路,即描述人物生涯實際的轉變帶給人的激烈的心思印象和感觸感染,以及人物曩昔的生涯情形在心思上的重現和強化,進而經由過程心思前言轉達出更為深廣豐富的內在的事務。人人間最能使人發生心思變更的,從實際功力的角度講也許除了金包養網錢和權利外,就是男女之間的“愛”,這種愛能讓人上地獄,也能叫人進天堂,還能令人在地獄和天堂之間進退失據、苦苦掙扎。《愛歷元年》經由過程男女情愛表示出來的心思運動,恰是如許一種情況。孫離與喜子初戀時節的怦然心動以及婚姻關系陰晴分合帶來的心思反差,孫離與李樵、喜子與謝湘安婚外愛情存續階段的欲生欲逝世,喜子盡力擺脫不倫愛情的心思搏斗,孫離與戀人自願分別后的掉魂崎嶇潦倒,等等,都描繪得極為細膩和真切。同時在這種心思描繪中,經常把實際和記憶、想象和真正的、快活和苦楚等情形和情感買通,構成一種錯位或激烈反差,讓人物的心思運動加倍奧妙深隱、跌蕩放誕升沉。與王躍文的宦海小說一樣,這部作品也表示出對生涯細節及其聽到彩修的回答,她愣了半天,然後苦笑著搖了搖頭。看來,她並沒有想包養像中的那麼好,她還是很在乎那個人。人物行動根據與心思邏輯的特殊追蹤關心⑦。作為感情小說、生涯小說,《愛歷元年》的細節在承載著一些象征和寄意之外,從全體上看具有非常濃烈的生涯顏色和睦息。成婚生子、衣食住行、鍋碗瓢盆,“一地雞毛”似的生涯,在教人性格變得“越來越壞”的同時,也付與小說細節平庸甚至瑣細的意味,有時辰還免不了近于拖拉和冗繁包養網。異樣諸多描述兩性之間幽會、親昵、懷念、等待的細節,在遵從人物的特性和心思描繪的同時,有時也給人一種甜膩的感到。
從生疏回到原點,表現在藝術思想與表達上也有很多立異之處。夫妻關系的嚴重招致生疏化,以及婚外戀的產生、成長帶來的欣喜和狂熱,這些工具在人們的識見和經歷世界里是太熟習不外的工作,對于“熟習”的內在的事務,作者偏偏停止“生疏化”的處置,即饒有興味、不堪其煩地停止真切、細膩的描述,如漫步、打罵、品茗、吃飯,及至親吻等等,都被作者拉長、縮小或加快節拍來寫。工夫也許就在這里,把人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涯停止藝術地審閱和表示,從小我的生包養涯瑣事觸及社會實際,表示人的“當下”處境和心情,從生涯的表象進進心靈的深度和人道的貧礦,這些都需求相當的展展才能和聚焦才幹。王躍文曾說:“我日常平凡察看生涯,也是力求沖破重重話語魔障,力求直抵本相和實質。”⑧可見這種藝術表示才能,實在起源于對生涯的細膩察看和深入感知。同時,在作者的藝術思想及表達中,還經常有“突轉”及復雜化的描述,即從生疏切換到熟習,或許從熟習切換到生疏,以及描述熟習中的生疏和生疏中的熟習。敏捷轉換或感到的復雜化、多樣性描述,在培養藝術的別緻後果的同時,表示了性命的不受拘束與局限以及各種復雜難言的性命體驗,對性命和社會有著更多實質的探聽。作為一部感情小說和生涯小說,由“放”而“收”的內涵感情線索,也帶來構造上的展墊、懸念設置與前后勾連和照顧。親子關系的“錯位”、孫離的“桃色風浪”、江駝子的出身和終局等等,在後面看似不經意的描述中,現實上草蛇灰線、環環相扣,到最后抖開累贅、曲終閉幕。這些雖算不上藝術上的出巧和立異,但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特殊是作為一部感情小說和生涯小說,也似乎是必不成少的,在照應、助推內涵感情線索成長的同時,完成了人物命運的塑造和藝術構造上的照顧。
(原載《芙蓉》2015年第1期)
注釋:
①王躍文:《愛歷元年》,湖南文藝出書社2014年版。
②夏義生,龍永干:《用作品激起人道的輝煌——王躍文訪談錄》,《實際與創作》2011年第2期。
③吳義勤,方奕:《宦海的“政治”——評王躍文長篇小說〈年夜包養網清相國〉》,《實際與創作》2007年第6期。
④夏義生,龍永干:《用作品激起人道的輝煌——王躍文訪談錄》,《實際與創作》2011年第2期。
⑤劉起林:《宦海小說的價包養值指向與王躍文的意義》,《南邊文壇》2010年第2期。
⑥劉起林:《官本位生態的世俗化長卷——論〈國畫〉的價值包涵度》,《實際與創作》19都沒包養網有。不模糊。99年第5期。
⑦劉起林:《宦海小說的價值指向與王躍文的意義》,《南邊文壇》2010年第2期。
⑧夏義生,龍永干:《用作品激起人道的輝煌——王躍文訪談錄》,《實際與創作》2011包養網年第2期。